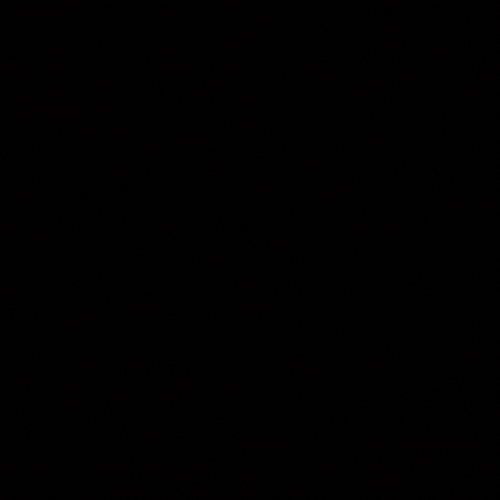是的回到这个问题,巴塔哥尼亚显然进入了那里;事实上,它是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但巴塔哥尼亚并不是我的研究重点。事实上,我一直尽量不直接。我写了三部以巴塔哥尼亚为领地的小说十一. 所以,对我来说,巴塔哥尼亚是我的文学领地,而不是环境或社会斗争的领地。这种情况在 年发生了变化,当时我亲自参与了反对水力压裂扩张的斗争,不仅在瓦卡穆埃尔塔,而且在我自己的家乡里奥内格罗艾伦,水力压裂目前正在取代梨和苹果的生产。我用私人钥匙写了一本书,从家庭经历到分析石油边界的扩张和人类世时期的社会生态危机。这是我最私人的书,一本介于散文和文学之间的书 . 无论如何,从 年开始,社会环境斗争促使我一方面去各省游览,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从大城市以外的另一个地方了解拉丁美洲。
年,我们与 以及 和 等同事共同发表了《跨国采矿、发展叙事和社会阻力》 , 这是第一本将阿根廷抵抗采矿问题系统化的书。当时,我们谈论的是采掘出口模式,但后来强加了“新采掘主义”的范畴,。 年,我们与来自不同背景的 建立了非常持久的联盟,他是一名环境律师。我们从为实现国家冰川法 荷兰号码数据 而进行的议会斗争开始,我们继续巡回领土约会,公开干预辩论,促进环境法和写书。同样从 年开始,我开始参与拉丁美洲规模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空间,讨论新提取主义的扩张、新的社会环境斗争或我所说的“生态领土转向”,以及替代视野,由安第斯地区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推动的发展替代方案常设工作组成员。这是我们开始讨论拉丁美洲进步进程的局限性的地方,重点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
个美妙的空间,对我来说仍然非常丰富,还有埃德加多·兰德、阿尔贝托·阿科斯塔、埃斯佩兰萨·马丁内斯、米里亚姆·朗等知识分子,还有许多年轻人,年轻的研究人员,如布雷诺·布林格尔、埃米利亚诺·特兰和许多其他人。因此,这曾经是并将继续是反思拉丁美洲的特权空间。我相信,而且我这么说并不是夸夸其谈,是我们把采掘主义问题和发展模式的讨论放在了区域议程上,质疑进步政府的局限性和漂移。 年至 年期间,我们发表了几项由非洲大陆众多左翼知识分子签署的声明,质疑委内瑞拉 [ á ] 政府和 [ ] -[ ] 的尼加拉瓜政权。所有这一切使我们与遵循自动声援进步政府路线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多冲突。